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1期
ID: 81739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1期
ID: 81739
戴望舒的诗歌艺术
◇ 王江辉
回望现代主义诗歌艺术长廊,我们发现戴望舒仍不失为一个正直的,流淌着新鲜血液的优秀诗人。他的诗歌中所内含的多种思想艺术质素,都显示着或潜存着新诗的发展与流变的种种动向。新诗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多少名噪一时的闻达者随着时光的流逝只剩下文学史价值,不再具备文学本身的价值,而戴望舒的诗虽几经命运沉浮,却始终魅力不减,风流了几十载,其许多作品至今为人称道,并用他不倦探索的足迹,为年轻的中国新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给后人留下了一笔艺术珍品和宝贵的艺术财富。
诗人戴望舒的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文学营养主要是,当时流行的欧洲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作品。1923年夏,他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开始接触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和浪漫派诗人雨果等人的作品,后与施蛰存创办《璎珞》旬刊,并开始正式发表诗作。1928年成为水沫社和《现代》杂志的作者群之一,创作现代派诗歌。之后又赴法国、香港求学,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1941年底,香港沦陷,被日本侵略者以抗日罪名下狱,数月后获营救出狱。抗战胜利后,他再度回到上海教书,1949年春北上至解放区,被推选为作协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理事。1950年2月28日,年仅45岁的戴望舒与世长辞。他一生收录成辑的诗作仅有93首,先后出版有《我的记忆》(1929年)、《望舒草》(1933年)、《灾难的岁月》(1948年)三本诗集,《我的记忆》和《望舒草》后由作者合编为《望舒诗稿》于抗战前出版。此外,戴望舒还有一些集外诗作和研究古典小说的文字,同时他还是著名的翻译家,在译介法国和西班牙文学方面作出过成绩。
一、戴望舒诗歌创作历程
纵观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大体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其早期的诗歌作品,多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流,情调比较低沉,有较多的感伤气息。他的第一部诗集《我的记忆》中,收录的作品大多都是情诗和愁诗。尤其是“旧锦囊”辑中留存的12首诗作,大体都是抒发这种个人哀愁感伤情绪的作品。如《寒风中闻雀声》中"枯枝在寒风里悲叹/死叶在大道上萎残"两句诗,勾勒出一幅枯枝败叶在寒风中飘舞的萧杀景象,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相似写照。再如《可知》中"可知怎的旧时的欢乐、到回忆都变作悲哀",《山行》中"见了你朝霞的颜色、便感到我落月的沉哀"等,都表现出作者早期创作的孤独、抑郁、伤感的浓重气息。1928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雨巷》,标志着诗人在新月派的影响之下由浪漫式抒情向象征式表现的一个转折,戴望舒也因此而赢得了"雨巷诗人"的美誉。
1933年由现代书局出版的《望舒草》表现了作者诗歌艺术的日趋成熟。此时的诗人生活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他的精神苦闷而低沉。但诗人不论从艺术上还是心理上都已不再稚嫩,也不再是穿着别人的鞋子走路,而是努力开拓自己的诗歌创作领域,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在《寻梦者》中,他写道:"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落了的时候",这支美丽的歌虽然依然流露着诗人疲倦的心境,然而却告诉了人们一个人生的真谛:任何美好理想的实现,任何事业成功的获取,必须付出一生的艰苦代价来追求。戴望舒在这一时期,虽然仍不失其孤寂、抑郁和多愁善感,但也不乏色调明朗、情绪奔放的诗作。如《祭日》、《游子谣》、《村姑》等。甚至在个别诗作中,我们还能读到诗人对于普通人民的关切和对光明的向往。如《流水》中:"在一个寂寂的黄昏里/我看见一切的流水/在同一个方向中/奔流到太阳的家乡去"。该诗充满了对生活的憧憬,对无往不胜的力量作了肯定,对顽强的生命力给予了热情的歌颂。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戴望舒的诗歌观念和创作实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决心在敌人的阴霾气候中挣扎,以自己微渺的光亮尽一点照明之责。1939年的元旦,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写出了《元日祝福》:"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祝福!我们的人民/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人民斗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唱出了诗人心灵深处真切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1942年,戴望舒被日本侵略军逮捕下狱后,他的个人命运更和祖国的命运交汇在一起,其诗风有了新的变化。《狱中题壁》抒发了诗人为民族解放慷慨赴义的勇气和胸有成竹的信心。《我用残损的手掌》是诗人在铁牢中唱出的属于"永恒的中国"的悲壮的歌:"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予爱和一切希望"。此外,《示长女》、《在天晴了的时候》表现了诗人在长年颠沛离乱之后,对于和平生活的渴望。其压卷之作《偶成》中"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表达了诗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总之,戴望舒后期的诗歌作品已显示出了超越个人情感的高层次内涵和蓬勃的生命力。
二、戴望舒诗歌艺术特点
戴望舒的诗歌作品虽然不多,而且大多都是短诗。但在诗歌艺术上,却呈现出了独特的成就与魅力。他的诗歌中所内含的多种思想艺术气质,都显示着或潜存着新诗的发展与流变的种种动向。新诗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多少名噪一时的闻达者随着时光的流逝只剩下文学史价值,不再具备文学本身的价值;而戴望舒的诗虽几经命运沉浮,却始终魅力不减,风流了几十载。诗人从汲取中国古典诗词的营养到采撷西方现代派手法,最终走向咏唱现实之路,几经寻觅和创新,形成了自己诗歌的特殊风格和色调。尤以其诗境的朦胧美、语言的音乐美和诗体的散文美为主要特色。
(一)诗境的朦胧美
戴望舒将法国象征派作为自己偷食的禁果,以此用来丰实自己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以象征化的意境和氛围传达感情,是戴望舒对中国现代派诗歌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象征派诗人追求的是把强烈的情绪寓于朦胧的意向中,主张诗要写得像“面纱后面美丽的双眼”,传达出内心的最高真实。戴望舒创作与接受的审美标准正是使诗歌处在表现与隐藏自己之间,即诗歌的朦胧美。在他的成名之作《雨巷》中,诗人构筑出一个富于浓重抒情色彩的意境,朦胧之美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地/我身旁这女郎/他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诗人把自己化身为雨巷中徘徊是抒情主人公,他在被朦胧细雨笼罩着的小巷中,内心怀揣着一个朦胧的愿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的姑娘",然而,她竟也默默无言,终是朦胧地、像梦一般地从诗人的身旁飘过,走进了寂寥的雨巷,留给诗人的是飘然而逝的希望。同时《雨巷》还是以古诗意象进行抒情的典范。它有浓郁的象征色彩,那孤独的"我"、梦般的"姑娘"、寂寥的"雨巷",都有强烈的象征意味;"雨巷"的泥泞阴暗,没有阳光与温暖,狭窄破败,正是沉闷窒息的黑暗现实的写照,皎洁妖媚又带苦涩的丁香一样的姑娘正是希望、理想与一切美好事物的假托。诗的想象创造了象征,象征反过来又扩大了想象,它使意境朦胧,一切都未明说一切又都在不言中说清,深得象征诗幽微精妙的真谛。用卞之琳的话说它是宋词《摊破浣溪沙》中"丁香空结雨中愁"一句诗的现代稀释与延伸。以丁香结象征诗人的愁心,本是传统诗歌的拿手好戏,在《雨巷》中却成为现代人苦闷惆怅的情思抒发机缘点;当然它也有超越传统的创造,古诗用丁香结喻愁心,它则把丁香与姑娘形象联结,赋予了艺术以更为现代更为丰富的内涵。它的意境、情调也都极其古典化,浸渍着明显的贵族士大夫的感伤气息,诗中映出的物象氛围是寂寥的雨巷、绵绵的细雨、颓圮的篱墙,它们都有凄冷清幽的共同品性;环境中出现的人也忧愁哀怨彷惶,默默彳亍冷漠惆怅,凄婉迷茫,物境与心境相互渗透交合,已主客难辨,情即景,景即情,它就如一幅墨迹未干的水彩画,稀疏清冷的图象后面潜伏着淡淡的忧伤与惆怅。象征派的形式与古典派的内容的嫁接融汇,形成了婉约朦胧的艺术风范。再如《印象》一诗 "是飘落深谷去的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小小的渔船吧 /如果是青色的真珠 /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林梢闪着的颓唐的残阳 /它轻轻地敛去了/跟着脸上浅浅的微笑/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 /迢遥的寂寞的呜咽/又徐徐回到寂寞的地方 /寂寞地"。这是一首纯意象诗。诗人抽去了语义上前后的因果关联,综合视觉、听觉、幻觉等各种类型的意象,借助一串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某种飘渺恍惚的记忆,其中有诗人对昔日记忆中事物的眷恋,也有内心隐藏的空虚和寂寞。诗中涉及的幽微的铃声、小小的渔船、青色的真珠、残阳、微笑、古井等,不仅是古诗中常用的意象,积淀着悲凉感伤的情思,而且内涵与情调也都具有同一指向,即它们都是稍纵即逝的美好事物,形断意连,意与象浑,构成了一个情思隐约,意境深邃朦胧画卷正如艾青在《诗论》中所说的那样"给情感以衣裳,给声音以色彩,给颜色以声音",使"流逝幻变者凝形"。戴望舒诗歌的朦胧之美正是通过意象的虚实和含蓄表现出来的。戴诗不仅在物象选择上常起用古诗中常用意象,自身充满迷朦、渺远、空灵之气;而且以意象与象征、暗示的联系建立,创造了意蕴内涵的朦胧美。尤其是在意象之间的组合上讲究和谐一致,所以常给人一种张驰有致的流动美感;而流动的便是氛围,这种情调氛围的统一、整合所造成的情境合一、心物相融,获得了浓重的朦胧美的审美特质。
[##]
(二)语言的音乐美
戴望舒曾说:“诗的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这笔触又是活的,千变万化的。” 这里所说的"巧妙的笔触"就是用艺术的语言筑造诗歌。戴望舒的诗歌语言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音乐美。
音乐美主要是指音节和韵脚的和谐、统一,使人的阅读朗朗上口、富有乐感。戴望舒第一辑《旧锦囊》中的十二首诗,都有明显的格律诗的特性,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新月诗派新格律诗的影响,句式大体匀称,每节行数相等,诗形整饬,押韵而且韵位固定,有的还讲究平仄相间。在《流浪人的夜歌》中,一共四节,每节三句,每句七字,且十分押韵。《断章》一诗更突出了诗人追求音乐美的特点。该诗一共八句,每句八字,分前后两节,且在诗中加入了古典诗歌所具有的韵味,极似一首婉约小令。杜衡在《望舒草·序》中说:“诗人追求着音律的美,努力使新诗成为跟旧诗一样可吟的东西”。在第二辑《雨巷》六首中,诗形也大多整齐,十分注重音乐性。例如《雨巷》,在梦幻与现实的不断交融中,ang韵反复出现,连绵不绝地织就了一张音韵的网,把人笼罩其中,好像在倾听一首低婉的吟唱。
值得一提的是,自第三辑《灾难的岁月》起,戴望舒受格律诗派的影响已明显减弱,而开始转到后期象征诗派的诗风上来。在他的《诗论零札》中,诗人认为:“诗不能侧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因此,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逐步从追求音律的形式中解脱出来,运用多种句式、灵活的手法来表达情感。如《旅思》一诗:“故乡芦花开的时候/旅人的鞋跟染着征泥/粘住了鞋跟,粘住了心的征泥/几时经可爱的手拂拭 /栈石星饭的岁月/骤山骤雨的行程/只有寂静中的促织声/给旅人尝一点家乡的风味"。这首诗前后两节分别以征泥、促织声为中心意象,以二者间的重叠与转换,展现了旅人落寞疲惫的心理状态和难遣难排的浓郁的乡愁 ,整首诗充满着含蓄效应,使外在物象成了内在心象的外化,成了“人化自然”。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诗人完全放弃了追求诗歌的音乐美,只能说明诗人在走向成熟的创作道路上,创作手法更多、更新,勇于用多种形式来丰富诗歌作品。从诗人后期的诗作《狱中题壁》中更能证明这一点,虽然此诗已注入了现实主义的内涵,也极具层次性,然而其整饬的句式和押韵,都流动出诗作所具有的音乐美感。因此说,不论诗人的创作风格如何变化,音乐美仍然是戴望舒诗歌艺术的特点之一。
(三)诗体的散文美
戴望舒从《我的记忆》开始,逐渐摆脱格律诗的樊篱,开始为自己制造“最适合自己走路的鞋子”,即以自由的散文化手法传达感情。这种现代口语形式的自由诗体,显示出了戴望舒诗歌所具有的另一种艺术美——散文美,这种创作风格也确立了诗人现代派诗歌的地位。
戴望舒从诗体上走向散文化,无疑对他在革新语言上产生影响,他用现代派的自由体抒情方式来表现诗歌的情绪,使诗歌显得更加朴素、自然、亲切。例如《我的恋人》:“她是一个娴静的少女/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出她的名字/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人"。诗人在平静的叙述中,使"我的恋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好像诗人用一支笔在轻轻地描画,让人一目了然又过目不望。诗人的另一首诗《村姑》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亲切的日常生活的描述,笔调舒卷自然,淳朴又富有韵味。诗歌《小病》是一篇散文化十足的华章,"从竹帘里漏进来的泥土的香 /在浅春的风里它几乎凝住了 /小病的人嘴里感到了莴苣的脆嫩 /于是遂有了家乡小园的神往......"。小病的旅人无聊孤寂,从浅春的泥土香里仿佛闻到了可口鲜嫩的莴苣味,于是勾起了对家乡小园的神往与思念。那么家乡的小园如何呢?诗人驾驭想象的彩翼飞抵它的近旁进行透视,那里阳光清澈和暖,细雨微风轻拂...... 一切平淡而熟悉,宁静而和谐 。诗人用猜测试探的语气,营构出一个小病的人对家乡的惦念关切。戴望舒诗体的散文化,不仅表现在描绘人物和事物上,还表现在其善于用短句来表达情韵。例如《灯》的最后一节:"这里/一滴一滴地/寂然坠落,坠落/坠落"。在《秋天的梦》一诗的结尾中:"唔,现在,我是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 诗中的这些精短简单的句子,虽然没有整齐的节奏和鲜明的韵脚,但在复沓的词语中形成一种千回百转的情愫,使读者感到诗句中内在情绪的流动,在娓娓到来的氛围中,给读者留出回味和想象的空间。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的那样:"语言能够流体化或呈现流线型,抒情诗歌就可以写到美妙的地方"。
当然,戴望舒的诗歌艺术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特点外,还具有其他方面的特色。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在诗歌中多种手法的运用。如通感、比喻、顶针、拟人、象征、重叠复沓等。《致萤火虫》中那句:“我躺在这里/咀嚼太阳的香味",历来被人们所称道,诗人奇妙地将视觉、味觉、嗅觉三者勾通在一起,并且将情思融汇于一句话之中。再如《秋蝇》一诗中"用一双无数的眼睛 /衰弱的苍蝇望得眩晕 /这样窒息的下午啊 /它无奈地搔着头搔着肚子 //木叶、木叶、木叶 /无边木叶萧萧下…… 。在立体化的流动的心理结构中,诗人用拟人的手法,通过描述秋蝇的形象,渗透出对日趋没落的现实世界的厌恶与自己作为政治殉葬品的无奈。这种多元素多层次的心理流程,映射出诗人的心理体验。它用重叠复沓的词语交汇出了幻觉、联想与情感活动,创造了一个全官感或超官感"心理格式塔",具有较强的纤细纵深感。总之,诗人借助于多种艺术手法,不断煽动着语言的斑斓的彩翼,给诗歌以美感、以生动、以光芒。
三、戴望舒诗歌中的不足
戴望舒在中国新诗史上,崛起于三十年代,上承中国古典文学之光泽,旁采法国象征诗派之芬芳,开启了现代派的诗风,确实引人注目。但就诗论诗,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诗歌中的一些不足。
(一)阴柔有之,阳刚不足
也许是才高气傲之故,台岛诗人余光中就认为戴望舒的诗的境界“空虚而非空灵,病在朦胧与抽象”,语言常“失却控制,不是陷于欧化,便是落入旧诗的老调”。这种观点虽然过于偏激和苛刻,但是纵观戴望舒二十多年的诗歌创作,虽然存在着阶段性的变化,然而他的诗歌作品留给我们的大多都是阴柔雅丽的。作为一个身处于国家危难之中的诗人,面对的是人民的苦难和自我的悲哀,应该有“直面人生的勇气”,用他多情的笔书写出人生的悲苦和悲壮,给人生以自嘲,给生命以勇气。而戴望舒的诗中“忧郁”、“抑郁”、“沉哀”、“哀怨”、“惆怅”等字眼屡现于各阶段的诗句中,难免给人以浅吟低唱之感。
(二)耽于情调,缺乏风骨
戴望舒是一个感情至上的抒情诗人。他主张在平淡的生活里发掘诗情,显示复杂微妙的情思颤动与飘然意绪,写出多元素、多层次的心理内容,“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不是去表现一种意思或思想,而是去表现一种幽深而又细微的感觉或情绪。受这种诗学思想烛照,他的诗也无不把感情放在首位,重视诗情的铸造。正如在他的《诗论零札》中,诗人认为诗的核心思想即诗情,认为“诗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这种观念就使得他的作品大多意境回肠,耽于情调,但却缺乏应有的现实风骨。尤其诗人面对抗日战争的残酷现实,虽然有《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反映现实的诗作,但也不能完全反映出诗歌的锐敏。或许是因为诗人多年来囿于自己的感伤世界,或许因为诗人盛年早逝,还来不及抒写更多的作品。
即便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诗人戴望舒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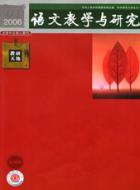
- 怎样使语文课姓语 / 徐百艳
- 解读语文教材中的生命意识 / 鲜志英
- 语文教学中的布白艺术 / 杨拥军
- 论叶圣陶语文教育的整体思想 / 耿红卫
- 蒙太奇与语文情境教学 / 余永刚
- 高中语文课改中存在的问题 / 胡平贵
- 戴望舒的诗歌艺术 / 王江辉
- 语文课的魅力何在 / 程正安
- 话题作文的两种拟题方法 / 任志福
- 语言连贯题的考试形式及解题技巧 / 余志明
- 语文教学中的言语品味 / 黄旭午
- 语文课堂教学的节奏调控 / 刘学成
- 诗歌的意象和意境 / 毛剑勋
- 立意思维训练模式探索 / 梁经伟
- 演讲辞开头六法 / 骆正军
- 话题作文的写作趋向与归宿 / 蒋新红
- 例说作文写作中的就地取材 / 任艳平
- 指导体验与自主性阅读教学 / 刘灿辉 吴神兵
- 让阅读回归阅读的本义 / 阮奕光
- 阅读教学中的探究互动 / 龚胜权
- 对中学生阅读习惯的调查与分析 / 李 健
- 文学批评与阅读教学 / 徐善慧
-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教学策略 / 秦 峰
- 《生命·生命》课堂实录及点评 / 张 琼 付 蓉
- 试析《庄子·逍遥游》的结构 / 田产东 杨慧俐
- 《促织》的情节构筑及抒情线索 / 王诗桥
- 《滕王阁序》美点撷谈 / 龚 伟
- 郑愁予《错误》的意象和情感 / 夏元明
- 从《祝福》中的重复性话语解读人物 / 唐登高
-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抒情诗吗 / 崔 雁
-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 / 王 琦
- 论语文备考中的七大关系 / 向汉波
- 《我与地坛》教学回眸 / 戢运宏
- 语文课堂拒绝戏说 / 王俊鸣
- 余映潮教学模式反思 / 彭红兵
- 高中语文教学形式主义批判 / 许典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