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4期
ID: 81639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4期
ID: 81639
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方法简论
◇ 方亚中
所谓“文论”,指的是“批评理论”、“理论”、“话语理论”以及现在广义上所说的文化理论。简单地说,“文论”就是关于文字(包括各种符号)和文本(包括社会文本)的理论。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冲击下,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的推动下,20世纪西方文论有继承、深化和改革的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创新、反叛和革命。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是批评家走向自觉的世纪,是文学批评走向独立的世纪。法国当代文学批评家让—伊卡·塔迪埃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一书中说:“在20世纪,文学批评首次试图与作为其分析对象的文学作品平分秋色。”研究20世纪西方文论,首先要抓住它的特点。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把当代理论归纳为“跨学科的”、“分析和思辨的”、“对常识采取批判态度的”和“内省性的”四个特点。其次,要注意文论的异质性和文学批评的转向,弄清文论发展的脉络。各种理论粉墨登场,既相异又互补。文学批评的转向往往以“跨越文化”的方式进行,新批评侧重于语义学,文学结构主义则整合人类学、语言学等更多学科,现象学和阐释学却同时是哲学的演绎,接受美学又联系到阅读心理学,它们都对传统批评的基础和设想进行空前的批判。第三,用文论进行文学研究时,需要有方法论的指导。方法的两级否定性、方法的层次性、方法的互补性,这些方法论中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文学批评同时是哲学的应用模式,文学批评同时又是文学理论。最后,要掌握并灵活运用各种文学批评方法。文学批评分为外在方法和内在方法;前者有精神分析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等,后者有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文体学批评等。此外,文学批评也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等。
一、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
我们通常把20世纪西方文论概括为“两大主潮”、“两次转移”、“两种转向”。文论中的“两大主潮”就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次转移”指的是文论研究经历从重点研究作者到重点研究文本的转移和从重点研究文本到重点研究读者反应和接受的转移。“两种转向”指“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这是文论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
从历史渊源来看,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原型。前者对理性逻辑的推崇和对归纳——演绎方法的倡导体现了科学主义精神;后者的灵感说和迷狂说带有非理性的神秘主义色彩,影响了人本主义思潮。20世纪西方文论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哲学上的经验主义批判和逻辑实证主义相关,其代表性文论流派主要是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人本主义文论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是19世纪叔本华、尼采所开创的带有浓厚非理性色彩的唯意志主义美学。受其影响,20世纪西方文论形成一股蔚为大观的人本主义思潮,其主要形态有:直觉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
如果按照战争的状态划分,20世纪分为二战前、冷战期和苏联解体后三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里,文论具有一种革命化的倾向,但在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中就出现了重视形式、排斥内容的形式主义。在欧美资本主义阵营里,一些知识分子除了吸收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成分外,还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柏格森的“生命自觉”,使文论呈现出精神分裂的非理性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更大,破坏性更大,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的信仰,焦虑、无聊、冷漠、绝望成了知识界和民众共同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怀疑精神作为支点的存在主义贯穿了二战的始末。这一时期的西方文论以新的研究方法和观念改变着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传统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进行猛烈的抨击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性,与此相伴随的结构主义、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也甚嚣尘上。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格局发展。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迈进,现代性也在向后现代转型;在这方面美国步子迈得更快,成为西方的中心。后现代主义以复制为特色,其典型艺术作品是随意的、折中的、混杂的、无中心的、不连贯的、拼凑的、模仿的,强调“文本互涉”或“互文性”,摒弃形而上学的深刻性,富于游戏性和享乐性。进入这一阶段,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论粉墨登场。大体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的西方文论受到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方法论的影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直接影响到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其次是社会的发展引起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因而引起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第三是社会条件的变化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实践,引起认识方式和理论方法的发展。对待西方文论,应该注意它们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强调关系和过程研究是各种西方文论共有的特点。
20世纪的西方文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和与之相关的文论,普遍抛弃了语言的表征模式,否定了语言是对现实的模仿、再现或反映。人并不是自由地支配语言,而是被语言支配,人一生下来就进入了“语言的牢笼”——一种先于他而存在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一种固定的关系网,决定了他的存在的地位,决定了他与自然、社会、历史、他人和自我的关系,也决定了他的行为及其与其他人交往的方式。之所以出现这种语言转向,是因为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后现代社会里,“居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将制造一个统一的、包括一切的、超星际的、为自动化而设计的组织结构。人不是作为自治的人而积极地发挥作用,而是将变成一种被动的、无目的的、由机器控制的动物,他们的正当作用……要么被机器吞没,要么因丧失个性的集体组织的利益而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人,他们不知道向何处去。以怀疑论哲学为基础的文论开始兴起,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达到了高峰;同时,为了强调个人意识的作用,对抗大系统结构的垄断和控制,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理论如接受美学或读者反应批评,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承认和发展。
20世纪文论发展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文化转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商品化的出现,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和营运方式,已经使经济权力开始危及到国家的统治,至少关于投资的部分决定超出了国家控制的范围。与此同时,知识的提供和应用变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知识一方面为商业开辟了新的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政治战略带来了新的挑战。于是西方出现了知识政治化的趋势,政治和各种机构竞相加强对文化的控制,结果在知识界激起了一股反垄断、反权威、反控制的浪潮,并由此激发文化研究,出现了从国家、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方面进行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
20世纪的西方文论还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概括和梳理。从话语影响看,20世纪西方文论表现出从知识性文化到意识形态性文化的变迁。从品格上来讲,20世纪西方文论显露了由诗学文化到文化诗学的跃进和拓展。从方法论角度看,20世纪的西方文论明显表现出从分析走向综合的趋势。从特征上看,20世纪西方文论呈现出从多元走向边缘的变迁。从发展趋势上看,20世纪西方文化是从吸收、对话走向发展的。
二、文学批评的外在方法和内在方法
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个方面,这是雷纳·韦勒克对世界文学界产生强烈影响的一个理论论点。这一划分的标准是整体结构与经验存在的区别。在韦勒克看来,文学作品是一种“意向性客体”。一方面,它既不是“真实的客体”,也不是“理想的客体”。由于每个个别接受者都有自己的“前理解”,有自己的个性心理特征,因此真正实现了或是“具体化”了的文学作品都带有自己的特点。文学作品必须经过这样的“具体化”过程才能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作为“意向性的客体”,又不等同于“经验的客体”。文学作品只存在于经验的事实之中,但却并不是事实本身。每个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经验固然有其不同,但毕竟可以相互比较。人们可以确切地知晓什么样的接受是相对为“正确”的接受,什么样的接受是“歪曲”的接受。所以,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意向性的客体”就是“由一些标准组成的一种结构”,“它只能在其许多读者实际经验中部分地获得实现。每一个单独的经验(阅读、背诵等等)仅仅是一种尝试——为了抓住这套标准的尝试”。这样,韦勒克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归结为“语言结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的对立。他将一切对文学作品存在本体“语言结构”的研究称为“内部研究”,而将一切与此无关、属于“经验存在”方面的研究称为“外部研究”。对文学作品具体存在的原因、效果和环境等的研究属于“外部研究”,它不同于文学作品“本体”和“结构”的“内部研究”,因为它是在经验领域中进行的。
[##]
因篇幅的限制,本部分只对读者反应批评和原型批评作简单介绍,前者属于外部研究,后者属于内部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方法和方法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这两者对研究女性主义非常重要。有人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主张,而不是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别的是女性主义独特的视角,而独特的视角只能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范畴。关于女性主义方法论,将在下一部分论述。
1.读者反应批评
纵观欧美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批评研究的中心经历了由作者到文本、又由文本到读者的转变。不过,严格来说,读者反应批评不只是注重读者本身,而是关注作者、作品和读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确定读者在文学中的作用、使文学批评研究方法发生转变的两位关键人物是德国的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分别发表了《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1967)和《文本的召唤结构》(1970),对结构主义文本中心论提出了挑战,否定了文本是封闭的、自足的系统,把文本看成具有开放性,具有接受、阐释的历史性,强调读者对实现文本意义的重要地位。
还有一位关键人物是美国的斯坦利·费什,他的两篇论文《文学在读者:感情文体学》(1970)和《阐释“集注本”》(1976)颇有影响,其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文学作品并不具有我们习惯的那种客观性,它是一种活动的艺术;与此相关,作品的意义也不局限在作品本身,而是阅读过程中的一种经验,是阅读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忠实地描述阅读活动,对读者的反应具体进行分析。他认为,在以上思想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关于读者反应的批评标准。
虽然读者反应批评家都认为读者在发现文本的意义上起着作用,但这种作用究竟是大是小则是有争议的,这就使得他们在批评方法的运用上具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按照运用方法的不同把读者反应批评家归为结构主义、现象学和主观批评三类,其界限还是很明显的,这样每一类之中的成员差别就不大了。第一类批评家虽然也承认读者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创造,但他们认为文本比读者对阐释过程更具有控制权。有的说某些阐释比另一些阐释更为有效,也有的将文本的意思(meaning)与文本的意义(significance)区别开来,把前者与作者的意图等同,而把后者看成是随语境或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杰拉德·普林斯的叙述学中,他区分了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对读者也分为真实读者、虚拟读者和理想读者。他的方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据文本分析,但由于对读者的关注,普林斯被列入读者反应批评这一流派。
现象学是一种强调接受者的现代哲学思潮。现象学者认为,物体只有在活动的意识(接受者)吸收或注意到它们的存在时才可能获得意义,换句话说,物体只在我们将之录入我们的意识的情况下才是存在的。罗森布拉特给诗歌的定义直接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真正的诗歌只存在于读者的意识之中,而不是在印刷的书页上。当读者和文本交流时,诗歌和意义也就创造出来了;它们只存在于读者的意识之中。阅读和文本分析现在变成了一种美学经验,在此,读者和文本在读者的意识中结合而产生诗歌。姚斯强调,在解读文本时必须把文本的社会历史考虑进去。他对读者反应批评的解释被称为接受理论。他认为,任何特定历史时期的读者都为自己设计评判文本的标准,他用“期待视野”这一术语将一个历史时期的批评词汇和对文本的评价包括进去,指出由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对文本评价方式必定也跟随变化。由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确立的期待视野,任何文本的整体价值和意义决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或是普遍适用的。这就否定了文本只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对姚斯来说,读者对文本的接受或理解以及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文本在解读过程中仍然是重要的,但读者起着最主要的作用。沃尔夫冈·伊塞尔对姚斯的观点作了补充,认为任何物体在活动的意识录入之前是没有获得意义的,因而要把被认识的物体与认识物体的意识分开是不可能的。运用这些现象学的概念作为他的读者反应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姚斯宣称批评家的工作不是分析或解释文本,因为一旦文本被阅读,物体与读者(接受者)从本质上将是一体的;批评家的作用就是研究或解释文本对读者的影响。伊塞尔还将读者区分为隐含读者和真实读者,通过假定隐含读者,他肯定了在解读过程中研究文本的重要性;同时,通过承认实际读者,他肯定了个体读者对文本反应的有效性。当文本被读者具体化时,读者将自动地根据自己个人的世界观观察文本。由于文本不可能讲述一切需要知道的情况,读者必须运用自己的知识自动地填补这些“空白”。
每个读者创造自己的期待视野,期待下一步可能或应该发生什么情况,这些期待视野不断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将使读者调整自己的视野,以适合于文本特殊的情况。在理解文本时,在填补文本空白时,在不断地采用新的期待视野时,读者运用自己的价值体系、个人的和集体的经验以及哲学信仰。根据伊塞尔,每个读者使文本“具体化”,因而每一具体化过程是个人的,它使得新的创造——文本的意义以及对读者的影响——变得独一无二。在解读文本中,读者是最主要的表演者;当故事被读、被具体化时,读者参与了文本的部分写作,成了合作的作者。
对主观批评家来说,读者的思想、信仰、经验在形成作品意义上比实际文本起着更大的作用。以罗曼·霍兰德和大卫·布莱奇为主要代表,这些主观批评家认为,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形成、并发现我们的自我身份。霍兰德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为其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提出了身份主题的概念。他说,我们出生时从母亲那里获得最初的身份,通过我们的生活经历,我们把这种身份个性化,使之成为我们个性化了的身份主题,我们就是用身份主题这个凸镜观察世界的。对霍兰德来说,一切阅读都是主观的,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种解读方法,因为阅读是一种主体经验。
布莱奇是“主观批评”的奠基者,他赞同霍兰德对解释过程中心理分析的解释,但他不重视文本的作用,否定文本的客观存在。他认为,意义不在于文本之中,读者在与其他读者的合作中产生文本的“集体意义”;每个读者只有在一个群体内能够把自己对文本的反应表达出来,这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群体才可能以合作的形式协商出意义,这种集体激发出的协商意义最终决定了文本的意义。因此,文本的意义过程分为两步,先是个人对文本的反应,接着是让这些反应接受社会群体的挑战,并对此进行修正、补充,然后才被接受下来,作为文本的意义。
2.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是流行于西方20世纪50-60年代的一个批评流派,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历史哲学家扬巴蒂斯塔·维柯(1668-1708)的《新科学》,一部对美学或艺术哲学具有转向意义的著作。在该书中,维柯曾提出神话理论,因此被称为是原型批评的“开路先锋”。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从历史的范畴解释了神话的性质和本质,把神话看成是“艺术前阶段”,是象征艺术原始时期的形成,为象征艺术开辟了道路。英国人类学家丹纳的《原始文化》和弗雷泽的《金枝》曾对原型批评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金枝》,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历史和宗教的范畴。原型批评的创始人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卡尔·荣格。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一样,荣格的以集体无意识学说为核心的心理学文论对文艺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早运用荣格理论的是蒙德·博德金,她于1934年发表了《诗歌中的原型模式》,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及原型理论运用于诗歌研究,继荣格、博德金之后,使原型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和手法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他在吸收神话理论、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了《批评的剖析》(1957),成为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弗莱对荣格的原型理论作了修正,在建立起自身批评理论的过程中,把对原型的定义从心理学的范畴移到了文学领域,建立了“以文学原型”为核心的原型批评理论,它的原型批评主要以荣格的精神分析学,尤其是“集体无意识”学说和原型理论为理论内涵,同时又吸收了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还出现了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理论,主要著作有安妮斯·普特拉的《妇女小说中的原型模式》(1981)、埃斯特拉·劳特的《神话制作者的妇女:二十世纪妇女的诗和视觉艺术》(1984)、埃斯特拉·劳特和卡罗尔·施顿尔·鲁普离希特合著的《女性主义原型理论:跨学科的荣格思想》(1985)。
[##]
所谓“原型”,指的是反复出现的一个情节样式、一个意象、一个描述的细节,或者是一个人物,这些能在读者身上产生强烈而又不合逻辑的反应。这一术语是通过卡尔·荣格的心理学著作引入到文学批评中的。荣格说:“原型即领悟的典型模式。每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我们就是在与原型相通。”他又说:“人的一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深深地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他认为,创作的过程就是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其进行加工制作,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荣格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三部分:个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带感情色彩的情绪组成,它构成心理生活中个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说的原型。位于心理深处集体无意识部分的是人类累积的知识,是人类对过去的记忆。这种知识通过人类重复的经验而形成,又可以通过生、死、再生、季节变化等意象挖掘出来,在文本中,又可以在读者身上产生深厚的感情。
在文艺研究中,荣格不同意文学艺术即幻想的特点,不赞成把治疗精神病的精神分析法直接运用于文艺研究。因此,弗洛伊德从“个人无意识”的角度去解释文艺现象,而荣格则用“集体无意识”理论去解释。荣格认为文艺作品是个“自主情结”,其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受作者自觉意识控制,而常常受到一种积淀在作者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的影响,这种心理经验就是“集体无意识”。虽然读者不能直接在文艺作品中发现集体无意识,但却能通过神话或图腾或梦中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发现它的存在和意义。因此,批评家可以通过分析在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或象征,重新建构出这种原始意象,进而发现人类精神真相,揭示艺术本质。
原型批评的显著特色是对文学的宏观分析和整体观照,其具体成果是从文学史上林林总总的文学现象中归纳出几种原型模式。其中,“死亡——复活”就是常见的一种模式,其特点是将英雄神话原型扩展为一种普遍的“生——死——复活”的循环模式。弗莱以主人公的能力大小及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为依据,将文学作品划分为神话、传奇、史诗悲剧、现实主义和讽刺五种基本类型文学类别模式。他还概括出文学的意义和叙述的辩证模式,认为文学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叙述运动,一是自然秩序之内的循环运动,二是自然秩序和启示世界之间的辩证运动。自然循环的上一半是传奇和天真类比的世界,下一半是现实主义(反讽)和经验类比的世界。由此可以得出四种主要的叙述运动类型,即传奇中的上下运动和经验中的上下运动。向下是悲剧型运动,向上是喜剧型运动。这样就有了四种文学叙述的基本要素,弗莱称之为叙述程式或类属情节。此外,母题研究也是原型批评理论的来源和基础之一。原型母题首先要具有古老的神话象征渊源,即与人类的原始仪式和亘古之梦相联系。其次是作为叙述代码,它具有很强的伸缩性,大可以接近叙述模式,小可以近似具体意象。在作品中它可以大于故事,即一个原型母题可以涵盖许多故事;也可以小于故事,即一个故事中可以含有若干原型母题。其三是具有广泛的交际性,在空间上它超越民族国家甚至文化圈;在时间上它跨越不同时代,具有长期延续性,而且不因具体时代的文学潮流和时尚而改变。这也体现了原型批评的文学人类学特点。
三、女性主义方法论
在女性主义者中,是否存在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或研究方法的问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虽然争议的结果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却让人看到了女性主义在方法、方法论与认识论这三个概念上纠缠不清。在《有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吗?》一文中,桑德拉·哈丁对此作了具有代表性的回答。哈丁首先对方法、方法论与认识论这三者作了界定:方法是指收集证据的技巧或处理方式,方法论是对研究如何进行或应该如何进行的论述和分析,而认识论则是关于认识及其本质的理论,特别是对认识的限度和有效性的研究。她指出,这三者是研究的三个方面,而在实际的运用上,“方法”一词经常笼统地用来指这三个方面;尽管关系密切,但它们彼此之间是有区别的。在社会学中,收集证据的方法不外乎三种类型:一是听被调查人诉说或向被调查人提问;二是观察行为;三是考察历史的踪迹和记录。这三种方法是没什么男女之分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同样也是使用传统上以男性为主的研究者使用的方法。然而,怎样运用这些方法收集证据往往明显地不同。例如,女性主义研究者会倾听被研究者的心声,听她们讲出对她们自己的生活和对男人的生活的想法,批判性地听她们讲述传统的男性社会科学家怎样将女性和男性的生活概念化等。不过,这里谈及的不是方法本身,而是方法论。方法论包括说明理论的基本结构怎样在特殊的科学领域中得到应用。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传统的理论在运用方式上难以理解女人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也难以理解作为社会性别化的男人的活动。她们也用传统的理论,但站在女性主义特定的立场进行表述,例如,在谈论如何运用现象学方法解释女人的世界、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女人在家庭或在付工资的劳动中继续受到剥削的原因中,我们可以找到女性主义方法论的例子。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女性主义对这些理论的运用能否对社会性别和妇女的活动作出完整的、没有被歪曲的解释,这是值得怀疑的。于是,女性主义认识论的问题就被引出来了。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的认识论系统地排除了女人成为认识者的可能性,科学的声音是男性的声音,历史是仅仅从男人的角度写出来的。她们提出替代的认识理论,使妇女作为认识者合法化。在澄清概念后,哈丁认为,不存在独特的所谓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只存在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舒勒密·雷恩哈茨将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归纳为十条:(1)女性主义是一种研究视角,不是一种研究方法;(2)女性主义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3)女性主义研究包括对非女性主义研究的持续批判;(4)女性主义研究是由女性主义理论所引导的;(5)女性主义研究可能是跨学科的;(6)女性主义研究以创建社会变革为目标;(7)女性主义研究努力代表人类的多样性;(8)女性主义研究常常将作为人的研究者包含在研究范围之内;(9)女性主义研究常常试图与被研究的人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互动关系;(10)女性主义研究常常与读者建立一种特殊的关联。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莉丝·斯坦利和苏·怀思将女性主义研究视为一种具有女性主义意识(feminist co ciou e )的研究,这种女性主义意识植根于女性独有的具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是女性对社会实在的独特观念的表达,因此他们强调只有女性才能成为女性主义者、具备女性主义意识并进行女性主义研究。但即使这样,他们也不认为存在什么独特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我们的立场是拒绝将‘女性主义研究’与某些特定的方法、性别主义(sexist)研究与其他不同的方法简单地等同起来。我们既不认为女性主义研究就是妇女所从事的研究,也不相信这种研究可以由男人来从事。因为我们觉得从根本上说,‘女性主义研究’是蕴涵着并产生于女性主义意识的,正因为如此它才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女性主义社会学家马乔里·德佛也认为,女性主义研究者主要是对现有的方法进行了修改,而不是发明了什么新的方法;但是他们的确已经形成了描绘研究实践和认识论的独特体系,这就是“女性主义方法论”。女性主义有许多种类型,因此其方法论也不是一些固定的教条,而是一种不断发展中的开放的对话。德佛认为这种方法论的核心就是批判,即将现有知识生产的工具视为建构和维护女性压迫的场所。
[##]
总之,强调其独特的方法论规则或研究视角构成了女性主义研究区别于非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而在研究方法上,女性主义坚持多元性和开放性,至于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女性主义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更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
注 释
[1][3][8][9][21]王逢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导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V—VI页,第VIII页,第IX—XI页,第VII页,第VII页。[2]张中载:《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前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II页。[4]参阅陈鸣树:《文艺学方法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53页。[5][12][13]参阅支宇:《文学批评的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0—22页,第90—91页,第97页。[6][10]参阅王松林编著《20世纪英美文学要略》,江西高校出版社,第364—65页,第367—68页。[7]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的神话》(1967年),转引自丹尼尔·霍夫曼编《当代美国文学导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7页。[1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第158页,转引自支宇:《文学批评的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0页。[14]张中载等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94页。[15]Charles E.Bre ler,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Third Edition), U 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3, p262.[16]参阅侯传文:《佛经的文学原型意义》,《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17]Sandra Harding,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In Sandra Kemp and Judith Squires (eds.), Feminis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 ,1997, 160-62.[18]Shulamit Reinharz,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 , 1992, p240,转引自吴小英:《当知识遭遇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19]Liz Stanley and Sue Wise,Breaking Out:Feminist Co ciou e and Feminist Research,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p31-32,转引自吴小英:《当知识遭遇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20]Marjoie L. Devault, Liberating Method: feminism and Social Research,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 , 1999, p30-32,转引自吴小英:《当知识遭遇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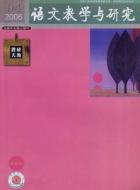
- 借助对句理解文言词语 / 蒋海鸥
- “伛偻病”与“佝偻病” / 张金发
- “忽悠”新义解析 / 王洪涌
- 语文教师课堂点评四法 / 彭山鸿
- 病句的辨析与修改 / 张红萍
- 现代文阅读赏析题干扰项命题特点分析 / 成 龙
- 课堂教学中学生评价的教育功能 / 李振林
- 论语文教学兴趣的触发点 / 肖海洋
- 语文学科校本教研活动的实践追问 / 杨舜山
- 语文课堂教学要以文本为中心 / 查德智
- 《项脊轩志》的几个细节分析 / 贾慧卿
- 《史记》的抒情特色 / 钱德宝
- 试析《漫话清高》中的几个难句 / 袁海林
- 站读《师说》 / 许国申
- 《石壕吏》体验性教学思路 / 徐雪贞
- 《蒹葭》三步赏读设计 / 张 花
- 《六国论》的多媒体教学构想 / 刘庆元
- 议论文写作的腹部开花技巧 / 艾永生
- 对另类作文应另眼相看 / 金 光
- 建立科学的作文评价体系 / 丁 群
- 实用主义写作教学浅论 / 钟沃林
- 音乐是解读诗歌的金钥匙 / 冯 杰 刘洪峰
- 阅读教学中的铺垫艺术 / 王唐平
- 古诗阅读教学中的探究性学习 / 刘 榕
- 阅读教学中的熟读与精思 / 王智勇
- 让学生与文本进行心灵对话 / 李舒怀
- 文学作品多元解读的思考与实践 / 谢银根
- 阅读教学中的破“隔”策略 / 陈益林
- 反思近几年湖北宜昌中考语文命题 / 万永翔
- 要警惕作文中的另一种声音 / 张新村
- 语文课应远离虚假的繁荣 / 宋卫邦
- 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方法简论 / 方亚中
- 语文教学应恰当使用多媒体 / 赖毓蓉
- 在生活中学习语文 / 冯惟勇
- 中国古典诗歌的虚实艺术 / 赵振民
- 语文新课程实验与审美能力的培养 / 崔干行
- 论语文教学的时代转型 / 雷业勤
- 吃好语文教学中的“鸡肋” / 庞晓阳
- 鲁迅小说人物命名探究 / 陈星际
- 语文课堂上的静默艺术 / 卢优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