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3年第5期
ID: 421515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3年第5期
ID: 421515
如何教学生用语文的方式学习语文
◇ 吴培贞
实行新课程改革以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代语文教学改革的一系列成果:对语文课程性质认识的不断深化,对语文课程基本任务理解的日趋完整,语文课程的形态建构有了新的突破,语文教学方法在不断改进,语文教学评价也在不断进步,教学日益成为一种复杂多向的交往过程,师生之间是平等对话和交互的关系,学生的主体地位越来越突出,而教师则逐渐成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咨询者和促进者。“语文素养”取代“语文能力”、“语文素质”而成了语文课程与教学的核心理念。人文性、语文实践、开拓语文课程资源、语文综合性学习也渐次成为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热点话语。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新课改下语文教学的课堂中出现的种种误区:“满堂灌”变成了“满堂问”;文本拓展“脱离了文本”,滑向了“泛人文化”;在所有语文课上都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课堂上虽然热热闹闹,学生却收获寥寥;许多老师搞“综合性”、“跨学科”学习,其结果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吸收了“新理念”,却忘了自己的“老传统”;进行“赏识教育”,说“你真聪明”、“太精彩了”,变成语文课上“学生无错”;教师缺位了……教师们越来越不知道该教什么和该怎么教了,误区成了走不出的怪圈。
笔者曾听过这样一节语文课,这是一节活动体验课,选自苏教版教材必修一中毕淑敏的《我的五样》。老师设计的教学步骤是:1.学生浏览课文;2.仿照课文选五样自己喜欢的东西(学生海选);3.不断舍弃其中的四样;4.学生交流展示,谈选择与舍弃的理由。学生的活动是:先浏览课文,进行选取、舍弃,然后小组进行交流选取与舍弃的理由。应该说教师对本节课的设计还是动了一番心思的,教学设计也是符合认知规律的。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在交流环节时有学生展示出他最终的答案竟然是“舍弃亲情,保留金钱”,并且振振有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答案?其根本原因在于学生不明白作者选择五样的内在逻辑“生存——生活——生命”,也就是说其没有认真阅读文本,不明白作者的选择过程——“空气、水、太阳、鲜花、笔”,其实就是追问生命存在意义的形象注解过程,作者舍弃的过程——“鲜花、水、空气、阳光”,也是在叩问生命的意义,作者之所以最终留下了“笔”,是因为没有了笔,就等于作家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思考、没有了批判,这样的生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的课尽管看上去热热闹闹,但学生的收获究竟又在哪里呢?又如史铁生《我与地坛》的学习,教师把教学重点放在了“如何面对逆境”小组讨论交流上,而对于这篇文章中史铁生在“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的残废了双腿”后的痛不欲生,以及他如何专注地在地坛想如何死的问题,在这古老而又充满无限生机的古园里,史铁生是如何找到自己精神安栖的家园,他怎样同自然对话、倾听心灵的声音、感悟生命的真谛,最终参悟出命运的玄机,完成了生命中最为壮丽的一次长达十五年的突围等等都视而不见,教师没有引导学生抓住地坛中的诸如“蚂蚁、蝉蜕、瓢虫”等景物具体分析,不扣住文本引导学生“抚摸语言”,体味语言的特点,而只是让学生谈假如你身处逆境时怎么办,让学生就此问题讨论交流,课虽上得轰轰烈烈,但没有了语文味,单纯地把新课程理解为就是加大人文性,弱化工具性。实际上语文课除了开拓思维这一点与其他各学科相通之外,还有培养听说读写和高尚情操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独有的特点。如果忽视了语文课的这些特点来进行拓展,就容易上成非语文课。
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应当是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以感受、思考、探究等方式,主动积极地实现建构意义、生成知识、获得体验、培育人格等目标的阅读实践过程。新课程下语文教学应致力于提升学生的生命质量,建构语文教学的内容、方法、过程,培养学生在学语文、用语文的过程中,对生命的认识、理解、体验,以生命哲学的思想指导语文教学,激励人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正因为此,所以笔者认为在新课程改革下要用语文的方式教学生学习语文。语文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以语文元素建构学习活动,换言之,就是听、说、读、写、思考、积累等语文活动。”
第一,语文课上有效落实文本的解读。
什么是文本解读?文本解读是指教师对文本(课标、教材和相关的课外阅读材料)的感知、理解和评价,进而产生感受、体验和理解并形成对文本材料的价值取向的一个过程,是阅读教学的准备阶段。在学校的各门功课中,语文是唯一以言语形式为教学内容的学科,而其他学科都是以言语内容为教学目的。对文本的解读首先要求教师自己对文本有深度地解读然后恰当地转化为教学设计,即教学内容、教学程序、教学方法的选择与安排;引导学生紧贴文本的地面行走,“在言语的丛林和字里行间穿行”,同时关注学生学情的分析。
如杜甫《江村》的教学:“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这首诗写于760年,诗人经过几年的流亡生活,来到了这不曾遭到战乱骚扰的、暂时还保持安静的西南富庶之乡——成都郊外浣花溪畔。他依靠亲友故旧的资助而辛苦经营的草堂已经初具规模;饱经离乡背井的苦楚、备尝颠沛流离的艰虞的诗人,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时值初夏,浣花溪畔,江流曲折,水木清华,一派恬静幽雅的田园景象。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享受江村生活的满足之情。然而诗人心里真的是快乐满足的吗?学生可能分析到此就已觉得把握了诗歌的含义,而这时教师就要进一步引导学生深层解读“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一句中“但”字的解释、“更何求”的含义。这两句虽然表面上是喜幸之词,而骨子里却饱含着不少悲苦之情。曰“但有”,就不能保证必有,诗人在诗中流露出担心这样的日子不能长久的忧虑,这样的生活是朋友接济的暂时安宁,是不能持续的,不会有真正的满足;曰“更何求”正说明已有所求,早年就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志,也发出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慨,诗句表达了诗人虽“有求”却无法实现的无奈。对于这首诗的分析,如果教师只停留在一般层面上进行解读,不引导学生扣住诗句紧贴解读文本的地面行走,那么学生就难以把握诗句的主旨,体会诗人的百姓情怀,了解诗人的愿望。正因如此,所以我们要明白:语文课就是语文课,要“得意得言”;语文课就是语文课,不要“走马观花”;语文课就是语文课,要“书声琅琅”;语文课就是语文课,要让学生“静心听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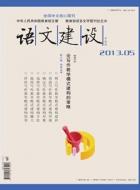
- 卷首 / 佚名
- 论写作教学模式建构的策略 / 彭小明 刘亭玉
- 如何教学生用语文的方式学习语文 / 吴培贞
- 语文的本质 / 荆含光
- 试析原型理论词典效应的延伸及应用 / 靳亚铭
- 元认知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 申向阳
- 语文教育中德育教育融入的意义 / 董骥 石茶 宋建卫
- 语言差异在语法教学中的对比性分析 / 黄永媛
- 注重有效激励,提高中职语文教学质量 / 邓建君
- 浅谈提高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汉语听说能力 / 阿不力孜·热扎克
- 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实践误区及改进措施 / 李建贞
- 基于语文教学目的的语用能力相关关系的辨析 / 易成俊
- 在网络背景下发展学生的多元智能 / 黎剑月
- 大学语文课外阅读教育的指导方法 / 周栋
- 新世纪我国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回归潮流 / 郭瑶
- 小说《那山那人那狗》抒情诗里的完美人生 / 温俊轶
- 美国田园梦的悲喜剧性破灭 / 王文婧
- 《老人与海》的原始主义倾向及禅意体验分析 / 姜风华
- 再论欧·亨利式的幽默 / 王先平
- 《聊斋》中的诗人形象分析 / 白波
- 海明威反战作品《丧钟为谁而鸣》人性缺失解析 / 慕容倜倜
- 《飘》的历史价值浅析 / 杨德洪
- 如果这样爱下去 / 孟晶
- 虚假的幸福,透支的人性 / 张建春 雷明珍
- 浅议《美妙的新世界》中的科学思想 / 田甜
- 略谈《宝剑记》中的家国情怀 / 朱红昭
- 文化转向和《老友记》中情感文化翻译 / 管振彬
- 比较诗学视角下论《等待野蛮人》的精神困境主题 / 周波澜
- 立足儒家兼采佛道——柳宗元对儒学的改造 / 李长海
- 杜牧诗歌的数字艺术 / 黄勇军
-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礼法观念冲突探析 / 汪荣 荣霞
- 近代汉语“好不X”格式语法构成研究 / 张海涛
- 先秦两汉时期量词的运用 / 王惠
- 《周作人诗全编笺注》中的几处笺注错误 / 常丽洁
- 标点修辞研究回顾与展望 / 牛淑敏
- 咬文嚼字,不厌其烦 / 冯雪冬
- 明清时期联合式复音词构成特点研究 / 毛向樱
- “可”作为不成词语素构词原因探析 / 郭沐
- 浅析我国汉语言学的继承与发展 / 孙和平
- 论语文美育的心理教化作用 / 李雪梅
- 从文学作品看音乐的发展 / 刘冠宏
- 浅析孔孟美育思想观对于大学生德育的启示 / 王向阳
- 我国历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和意义 / 时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