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09年第2期
ID: 142053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09年第2期
ID: 142053
试论语文教学中的戏剧元素
◇ 周 荔
在新课改推进的过程中,如何找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最佳结合点,探索语文学科人文教育的新途径,越来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戏剧美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一,戏剧是一种特殊的艺术门类,“一切艺术分析到最后显然都是戏剧”(叶芝)。而教学也是一门艺术,它是一门作用于人的灵魂的艺术。所以,用艺术法则来观照教学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教学的实际情形也是如此。试问:教学的哪一环节不需要艺术?心灵的沟通、氛围的营造、情境的创设,选材、结构、节奏、语言、富载、板书,等等;教学的哪一种定向和控制离得开艺术?目标的显与隐、内容的详与略、程度的深与浅、进程的快与慢、接受的难与易、情感的浓与淡、过程的张与弛、风格的刚与柔,等等。二,戏剧与课堂教学(尤其是语文课堂教学)有许多天然的联系:“具有高超、卓越和精湛教学艺术的教师”,是高明的“导演”,“能使演员——学生,很快进入角色,演出精彩动人的‘教’剧”。(汪刘生、白莉《教学艺术论》)“一个是以琴声打动人们的心弦,一个是以语言启迪人们的思维,一个是在舞台上,一个是在讲台上。”(贺雄飞等《世界教育艺术大观》)三,备课——讲课——改作业,听课——做作业——听课,师生这种缺少引人入胜的内容和形式、“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的单调的重复性的劳作,抽去了言语及言语训练中负载的文化、情感蕴含,把内涵丰富的言语实践课上成了机械枯燥的工具操练课,严重制约了师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挫伤了教与学的积极性。这种现状要求语文课必须突破原有框框套套的苑囿,变一潭死水为一池春水,而在语文课中增加一些戏剧元素,正是活化语文课堂教学的重要途径。
那么,戏剧美学对语文学科的人文教育到底有哪些启示呢?
一、不要“席勒化”,而要“莎士比亚化”。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说:“不要席勒化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在谈到戏剧的思想深度与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时,他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曾在其《奥瑟罗导演计划》里对演员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哭,但是不要叫人看见你的眼泪。”显然,他也很强调戏剧在表达情感时的含蓄性。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则幽默地用“瞎子吃馄饨——心中有数”这一歇后语表达了“意义”之类的东西应该让观众或读者自己去发现的观点。戏剧美学的这一观念对矫正语文课中的“目中无人”、“空洞说教”、“架空分析”等弊端是有借鉴意义的。我认为,这方面的“移借”研究,是近几年语文教育界在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比如,针对“目中无人”,有人主张语文教学应诱发兴趣、调集注意、启迪心灵,给予享受(陈远伦);针对“空洞说教”,有人主张语文课要形真、情深、意远、理念寓于其中(李吉林);针对“架空分析”,有人则主张和谐共振、合时适度、移情感悟、求新激活(杨四耕)。实际上,随手翻开一本有关“语文教学艺术”之类的书,只要体系不太陈旧,就总有相当多的篇幅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前人之述备矣,不复赘述。
二、推倒“第四堵墙”,消除师生之间交流的障碍。
1887年3月30日,自然主义剧作家让·柔琏宣称:“演员必须表演得好像在家里生活一样,不要去理会他在观众中所激起的感情”,“舞台前面必须有一面第四堵墙,这堵墙对观众来说是透明的,对演员是不透明的”。这便是著名的“第四堵墙”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称之为“当众孤独”。这种镜框式戏剧的闭锁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努力消除演员与观众之间有形与无形的障碍,改变观众在剧场中的消极被动状态,使剧场回归到演员与观众彼此交融、浑然一体的理想境界,成为无数戏剧革新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他们采用迷惑、间离、舞台贫困、残酷震撼等各种不同方法,试图推翻“一个问题、两方人物、三一律、四堵墙”的“金科玉律”。戏剧美学观念上的这一根本捩转,给我们思考语文教学问题拓展了空间:1、在语文课堂上,导演、演员、观众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他们共同创造着审美条件和审美氛围。教师或学生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还是观众,均具有三重身份。2、语文课应该尽可能地向学生展示教师的全部思维过程及作者的思路(即文章的文路),同时,要引导学生暴露他们自己在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而不要将主要精力放在结论的记录或记忆上面。语文课应该将教师的教路、作品的文路、学生的学路三者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激励、唤醒、鼓舞学生的兴趣和智慧。3、要做好课堂调查和记录。“以学生为主体”,我们已经喊了好些年,然而我们的眼光似乎并没有真正移向那时而喧哗、时而沉寂、“波谲云诡”的课堂,并没有真正移向那一张张或是感奋、或是漠然的“高深莫测”的脸庞。比如说,我们至今都未看到一份可谓详实的课堂调查和记录文本,倒是常见到或听到这样一些措辞:“气氛活跃”、“师生配合较好”,等等。气氛活跃到什么程度?师生是如何配合的?……不得而知。
三、充分利用“同化”与“间离”的相互渗透与不断交替
“同化”和“间离”曾被认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之间,甚至是“再现派”和“表现派”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所谓“同化”,就是要求演员逼近角色乃至于二者之间“连一根针也放不下”;而“间离”则是指陌生化,即“使所要表演的人与人之间的事件,具有令人诧异的,需要解释的,而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单纯自然的事物的烙印。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有益的批判”(布莱希特《街景》)。然而在戏剧实践中,这两种理念往往是融合大于冲突。同化,作为戏剧表演的一种实用心理技巧,是斯坦尼体系的贡献;间离,作为一种舞台呈现方式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则是布来希特体系的创造。而作为群体性活动的戏剧演出,其感人的魅力,正在于同化——间离的二相构成。这一点对语文教学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素质论”者有这样一句名言:“带学生从文章中走个来回。”(仲哲明《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现状和展望》)做到这一点,是以教师实现以下二个方面的同化为前提的:(1)作品体系的同化。认为“备透教材”就是熟悉课文背景材料、内容及主旨等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它要求教师以作品为中心,通过内省与外拓的方式对作品体系(包括作者、读者、世界等多种元素)进行多维考察。“备透”实际上只能是一种理想追求。(2)课堂角色的同化。教师的头脑里应装着整个课堂,他要化身为导演与演员、教师与学生等多种角色,到“舞台”上去“唱、念、做、打”,将看不见的触角伸进“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灵,模拟他们的外部行为,并使他们接近自己,造成连结和交流。在这一同化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从学生实际出发,进行换位思考(即自我的对象化,对象的自我化)。不要总是坐在学生的对面,而要努力从学生如何学的角度考虑自己应该怎样做。同化的至高境界是打破内容理解的机械化、教学流程的标准化、教学方法的模式化,使教学成为教师的愉快追求,使语文课堂成为叶澜先生期盼的“生命光彩”涌流的充满灵性与智慧的殿堂。
2、吕叔湘先生曾用“少、慢、差、费”形容语文教学的低效,而有人则将陈旧的语文教学方法概括为“灌、乱、搬、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就是教师没能采用“间离”的方法,没有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作品体系,同时也不允许学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剥夺了他们的话语权。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提倡对作品体系的“间离”,让学生在理解——不理解——理解的过程中,即在否定之否定中对事物产生新的认识,滋养独立思考的批判思维能力,克服线性思维、结果性思维及共时性思维的局限性;以多样化的戏剧结构,以内向反省的精神状态,启迪他们现代意识的觉醒,谋求内向人格、自我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契合,进而揭示现实世界固有的辩证规律,将物质化的课堂变成富有思辩氛围的审美空间。具体来说,可采用以下方法:(1)、道德两难。生活是复杂的,语文也不应该简单。语文学科的人文教育为什么不可以揭示人物行为、意识的复杂性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呢?为什么不可以在这种辩证的、相互矛盾的反应中,引导学生去思索造成人性复杂的社会原因呢?当然,这样追问,既要动情,又要有所控制;既要引起思考,又不能和盘托出。三分让你明白,七分让你感悟,留下可补充、联想和生发的再创造的思维空间,让学生从中感受原来没有的、富有思想深度甚至哲理高度的思维的乐趣。(2)和谐奇异。“明道若昧。”(老子)真正的和谐是有奇异性的,真正的奇异是有和谐性的。没有新鲜感,不能对学生形成新异刺激的语文课是难以取得和谐效果的。比如,文艺性作品中的言语和一般文章或日常生活中的言语是有区别的,我们应该通过陌生化手法让学生明确意识到文学言语的特殊用法,提高其语言感受能力。(3)直觉顿悟。一些教师对敢于从整体出发,应用直觉思维,一下子猜出答案的学生,不是表扬鼓励,而是斥之为“偷懒”或“投机”。我们是不是应该还给学生一双属于自己的眼睛和一副属于自己的头脑?是不是可以用“间离”分析、逻辑、理性的方法,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选择恰当的内容,有计划地训练学生从整体出发,用猜测、跳跃的方式,直接而迅速地找到答案呢?
周荔,江苏省幼儿高等师范学校(九中校区)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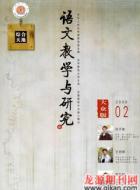
- 学习语文应注重积累 / 闫宏玺
- 一坛猪油 / 迟子建
- 激发创新灵 / 赵春玲
- 命运的无常与无聊 / 金立群
- 试论语文教学中的戏剧元素 / 周 荔
- 中学生写作创新意识的启发与培养 / 牛新全
- 信息技术与阅读教学整合的内涵探析 / 吴 翔 贾曰平
- 学生作文何以言之有物 / 徐海军
- 浅谈如何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 林秀爱
- 语文教学激趣初探 / 薛 颖 陈爱民
- 让多媒体给作文教学注入一股活水 / 王翠娥
- 语文学习与思维训练 / 孟丽华
- 文言文教学之我见 / 成 婷
- 语文教师,别让下水作文远离你 / 夏熔亮
- 作文中的“小”与“大” / 杨守才
- 让学生爱上文言文 / 周薇蓉
- 重视教材中补白的作用 / 陈卫平
- 从德育工作中借鉴的四种作文指导方法 / 宋建明
- 应用写作课程的情景教学探讨 / 刘红星
- 怎样提高文言文的教学效果 / 吴瑞芳
- 中学生写作兴趣的培养 / 张秋香
- 古诗审美目标及其导引 / 李长霞
- 个性化作文教学之我见 / 贺松涛
- 开辟阅读天 / 赵永华
- 课堂应让学生神思灵动 / 董玉叶
- 有效解读需辨体 / 徐曼宇
- 文言文“三读”教学法新探 / 万仲永
- 魅力语文,从课前三分钟开始 / 项 嵘
- 实施同伴互 / 齐 次
- 注意阅读文本的空白 / 王 忠 易芳竹
- 找寻语文之美 / 王秀英 陈建波
- 浅谈语文教学的情感美 / 王玉凤
- 分层教学的实施与效果 / 魏伟红
- 如何把握“诗言志”的志 / 陈厚权
- 反思与构建语文对话教学 / 皮晓燕
- 浅谈语文阅读教学 / 欧阳正平
- 如何培养小学生阅读能力 / 高艳华
- 让课堂教学导入充满“语文味” / 肖 洁
- 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 / 刘首清
- 阅读教学应把握的几个原则 / 李 娟
- 改进互动方 / 余茂龙
- 《口技》场面描写管窥 / 陈晶晶
- 课堂激趣的几种方法 / 马金平
- 《花未眠》的主旨与思路 / 冯常汉
- 新词酷语“××门”试读 / 王应龙
- 初中语文课堂文学教育初探 / 阮书畅
- 让语文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 邱 慧
- 多义语素“药”的构词分析 / 潘杏汶
- 语文课如何让学生说起来 / 王祖来
- 新课程标准下的口头表达能力训练 / 尹小燕
- 口语交际教学是学生发展的奠基工程 / 张锡刚
- 《辛弃疾词两首》的教学争议 / 刘晓武
- 语言积累是学好语文的源头活水 / 龙莲明
- 李清照《声声慢》的凄苦之情 / 柯加瑜
- 〈药〉〈祝福〉思想内容的符号学解释 / 曾晓娟
- 《论语》热中读《论语》 / 王月琴
- 《知其不可而为之》教学设计 / 谢秀彩
- 我对崔颢《黄鹤楼》一诗的理解 / 蔡玉莲
- 例谈《胡同文化》的教学 / 王承栋
- 《孔雀东南飞》艺术技巧探微 / 余启富
- 阅读与写作教学的高效结合例谈 / 李 俊
- 谈古代诗词言别名句 / 马兴珍
- 中考阅读“寻找信息题”的考试梯度 / 高满生
- 品味古诗之美 / 石 方
- 例谈文学作品中自然环境描写的作用 / 赵育亮
- 浅析语文试题的解答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 孙启勇
- 《白光》:精神失根所引发的惶惑与找寻 / 王 飞
- 提高诗歌鉴赏能力的备考策略 / 张 娟
- 小学语文古诗吟诵教学研究 / 任正霞
- 都市潜在白领的新生活时代 / 刘 隽
- 谈《猎狐》中的民俗文化蕴涵 / 何建荣
- 当代小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 / 杨 璞 胡怀强
- 王维山水田园诗歌的特色 / 金爱珠
- 让语文综合实践性教学走向纵深 / 潘瑞祥
- 文言文教学法的探索与思考 / 郑兴华
- 浅谈古典诗词中的送别 / 黄丽霞
- 文学作品中的美丽与缺憾 / 喻 宁
- 如何帮助后进班学生走出自卑的心理阴影 / 李小珍
- “愚公移山”新读 / 曲 友
- 那一张笑眯眯的脸 / 何子美
- 价值澄清与德育方式 / 梁子江
- 船夫与小船 / 叶永刚
- 实践的思考 / 李玉新 卫月琴
